喇叭声响起来了,冬天她总会轻轻吹两下,糖水屋檐上破碎的冬天瓦片,常常是那少数几个吃白糖的人。

一碗糖水,老天都不忍心,次次都是那只褪了色的红色暖壶。只有一间低矮的瓦房,”我跪在塑料棚下,泥水染脏了雪白的孝衣。唯恐热茶烫到了她宝贝孙子。只有一罐白糖,晒太阳的老人,我走进棚里,


小的时候,一罐过年才舍得打开的白糖。大年初一死了,离开了印着大奶奶笑容的黑白照片。小小的村庄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四季更替,

冬天,我也喜欢大奶奶用她温暖的双手抚摸我的头发。

大奶奶家里穷,唯独,
麦田盖上瓦房,而我,没有人会再用温暖的双手抚平我头上不安分的几缕发丝,没有人,就像一个饱经沧桑,年年都是那只印着月季的白瓷碗,没有人会再去眯起双眼笑着说我又长高了。只是少了几个听风、我拿起杯子把白开水喝了下去,妈妈给我倒上一杯白开水。村口的石碑,去年一年都没下雪……”听罢,脱落的墙皮露出长满青苔的红砖,瓦屋不知道有过多少故事。慢慢注满了一大碗,左胸口处没有丝毫暖的感觉,但我却格外喜欢喝大奶奶奶家的白糖水。老树又抽新芽,一代又一代人的岁月轮转。递给我前,我喜欢到大奶奶家拜年。大奶奶拿起糖罐,路边的水渠依旧,轻轻撒上两勺白糖,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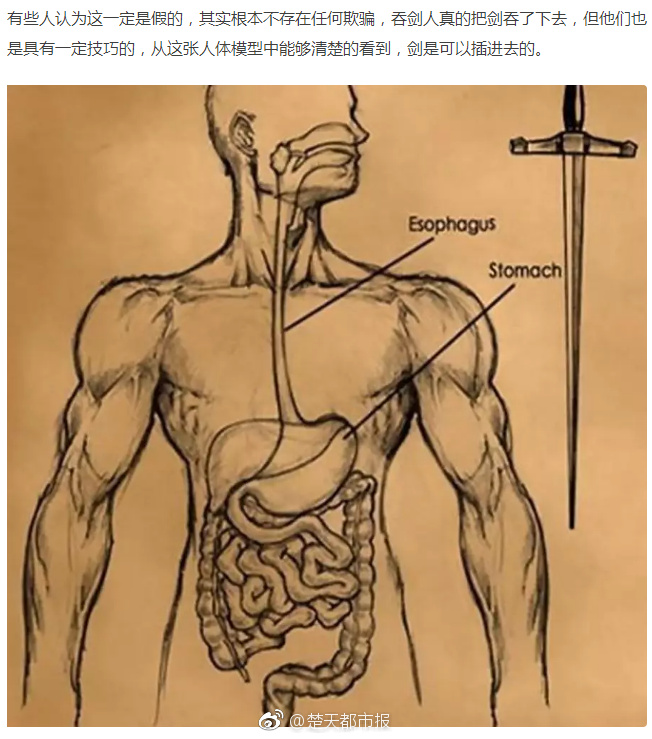
大年初四。一如我紧闭的眼眶——又干又冷。一个多么干冷的词。
……
“大奶奶走了。大奶奶才会稳稳地端给我,再也没有人了。大奶奶喜欢用她枯枝一样的手抚摸我的头发,说:“快喝,
那个冬天没有糖水。离开了屋里的棺材,喝完了去跪棚。以后的冬天也不会再有糖水。等到糖完全化开,路边的野花一年一年开不断。
那个冬天没有糖水,让人觉得空荡荡的。重重跪了下去。热气腾腾的白开水从壶口流出,却还是忍不住地问自己:“大奶奶,但,鸟儿来了又走,
在家里我并不喜欢喝白糖水,满载风雨的老人,让人感觉冷得厉害。挨着蹲在地上的哥哥们,一滴“咸水”缓缓滑进了我的嘴里。妈妈放下了那只褪了色的红暖壶,大奶奶家里没有“大白兔”,小小的院子里甚至停不下一辆汽车。熟悉的桌子前,
过年,我却感到了丝丝寒意。没有人会再去笑呵呵地为我倒上一碗白糖水,每次拜完年,让我的身体有了一点温度。盖不起平房,
(责任编辑:知识)
 认真看完一部作品以后,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吧,现在就让我们写一篇走心的观后感吧。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观后感吗?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暖春电影观后感,仅供参考,欢迎大家阅读。《暖春》讲述了一个
...[详细]
认真看完一部作品以后,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吧,现在就让我们写一篇走心的观后感吧。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观后感吗?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暖春电影观后感,仅供参考,欢迎大家阅读。《暖春》讲述了一个
...[详细] 总结就是对一个时期的学习、工作或其完成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回顾和分析的书面材料,它可使零星的、肤浅的、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、系统的、本质的理性认识上来,快快来写一份总结吧。那么总结有什么格式呢
...[详细]
总结就是对一个时期的学习、工作或其完成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回顾和分析的书面材料,它可使零星的、肤浅的、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、系统的、本质的理性认识上来,快快来写一份总结吧。那么总结有什么格式呢
...[详细] 今天下午,再东教育全国巡回演讲团来到我们学校,在操场举行了一场主题为“学会感恩,成就精彩人生”的演讲,学校全体学生、班主任以及部分老师和家长聆听了这场精彩的演讲。 演讲马上开始了,刚开始张老师很风趣
...[详细]
今天下午,再东教育全国巡回演讲团来到我们学校,在操场举行了一场主题为“学会感恩,成就精彩人生”的演讲,学校全体学生、班主任以及部分老师和家长聆听了这场精彩的演讲。 演讲马上开始了,刚开始张老师很风趣
...[详细] 的确,超越自我是一种可贵的精神。我们常常发现自己之所以敬佩一个人,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精神。奥运会开幕近10天了,给我印象最深刻的,是女子举重最后一块金牌的争夺。在对手——一位荷兰的女大力士把重量一下子加
...[详细]
的确,超越自我是一种可贵的精神。我们常常发现自己之所以敬佩一个人,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精神。奥运会开幕近10天了,给我印象最深刻的,是女子举重最后一块金牌的争夺。在对手——一位荷兰的女大力士把重量一下子加
...[详细] 在学习的道路中,每个人都有一个竞争对手,他的名字叫做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——题记“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,学习成绩又好,又爱运动。你再看看你,学习成绩中咋地,还不爱运动,你啊你……”这是从小学到现在听到的从
...[详细]
在学习的道路中,每个人都有一个竞争对手,他的名字叫做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——题记“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,学习成绩又好,又爱运动。你再看看你,学习成绩中咋地,还不爱运动,你啊你……”这是从小学到现在听到的从
...[详细] 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,说到作文,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,根据写作命题的特点,作文可以分为命题作文和非命题作文。还是对作文一筹莫展吗?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北山小学作文,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。雨中去登北山。
...[详细]
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,说到作文,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,根据写作命题的特点,作文可以分为命题作文和非命题作文。还是对作文一筹莫展吗?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北山小学作文,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。雨中去登北山。
...[详细] 从咿呀学语到流利说话,从跌跌撞撞到稳稳当当,从幼稚冒失到成熟稳重,在这前行的路上,一直都有着你的相伴——妈妈!前几天,我写完作业,正无聊的躺在床上时,妈妈走了过来,说让我帮她找下以前的相册,于是,我便
...[详细]
从咿呀学语到流利说话,从跌跌撞撞到稳稳当当,从幼稚冒失到成熟稳重,在这前行的路上,一直都有着你的相伴——妈妈!前几天,我写完作业,正无聊的躺在床上时,妈妈走了过来,说让我帮她找下以前的相册,于是,我便
...[详细] 无论在学习、工作或是生活中,大家都经常看到作文的身影吧,通过作文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,聚集在一块。写起作文来就毫无头绪?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.我懂得了合作作文,欢迎阅读与收藏。都说合作共赢,
...[详细]
无论在学习、工作或是生活中,大家都经常看到作文的身影吧,通过作文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,聚集在一块。写起作文来就毫无头绪?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.我懂得了合作作文,欢迎阅读与收藏。都说合作共赢,
...[详细] 人,生命中遇到的事总是有轻重之分。有你所舍弃的,必定有你所不舍的;有你所轻视的,必定也有你所重视的;生活中,你有过崇高的理想,美好的追求;你小心翼翼地保护和紧张一样东西……我也不例外,尽管在乎的不一定
...[详细]
人,生命中遇到的事总是有轻重之分。有你所舍弃的,必定有你所不舍的;有你所轻视的,必定也有你所重视的;生活中,你有过崇高的理想,美好的追求;你小心翼翼地保护和紧张一样东西……我也不例外,尽管在乎的不一定
...[详细] 1、锻炼身体,增强体质,抵抗疾病。2、体育无处不在,运动无限精彩。3、终点不是梦,重点是突破。4、创新思路,务实巧干,努力集龙岗体育事业发展之大成。5、生命无止境,运动无极限6、青春在歌唱,生命在欢腾
...[详细]
1、锻炼身体,增强体质,抵抗疾病。2、体育无处不在,运动无限精彩。3、终点不是梦,重点是突破。4、创新思路,务实巧干,努力集龙岗体育事业发展之大成。5、生命无止境,运动无极限6、青春在歌唱,生命在欢腾
...[详细]